当浦东的芦苇荡在时代浪潮里抽出现代化的新芽,当一位作家用八年光阴续写一片土地,文字便成了丈量历史的标尺。
作家何建明所著的《浦东新史》,承续《浦东史诗》的笔力,是对浦东开发的又一次深情回望,更是对“中国式现代化”的文学注解。
在与何建明的对话中可得知,所谓“新史”,并不是简单的时光记录,而是告诉后来者,这片土地如何从泥泞里生出力量,如何在挑战中开出新局。
梦与根的交织
上观新闻:您的《浦东史诗》和《浦东新史》两部作品,像两把钥匙,解锁了浦东发展的壮阔画卷。很多读者好奇,您与上海这座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结,能让您倾注如此多的心血书写它?
何建明:上海对我来说,是刻在基因里的牵绊。这种牵绊不是凭空而来的,而是从祖辈的故事里一点点渗透到骨血中的。我的曾祖父是清末时期从苏州来到上海的,当时的上海还没开埠,黄浦江面上全是摇摇晃晃的木船,码头边全是等活儿的苦力。曾祖父力气大得惊人,据说他一个人能扛800斤货物,就靠在码头上扛木头、运石料谋生。后来他和几个同乡一起搞起了“贩树”的生意——那时候造船需要大量木料,他们就从苏州运树到上海,便成了十六铺码头和浦东“和记码头”的常客,久而久之便将浦东视为半个家。
然而,由于一位苏格兰商人所建造的一家火轮船厂开始在浦东出现,浦江两岸的诸多本土木船厂纷纷倒闭,我曾祖父也就回了老家。这段家族史,我从小听到大,总觉得浦东的土地下埋着我们何家的根。我在苏州长大,但后来几乎每年都会跟着父母到上海来。第一次来上海时我才五岁,在第一百货商场里转得晕头转向,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,觉得这城市像个万花筒,神奇得让人着迷。
真正让我对浦东产生“宿命感”的,是一次意外。大概十岁那年,我跟着父亲坐小船从苏州河到黄浦江,想看看爷爷说的“老码头”。那天江面上船特别多,我们的小船靠父亲他们摇橹前行,在宽阔的江面上漂荡,有些无法控制,随后被一艘大船撞翻了,我抱着一块木板漂了好久,最后在靠近外滩的地方被人救起。趴在岸边吐水时,我抬头望见对岸的浦东,全是芦苇荡和低矮的农舍,跟外滩的繁华完全是两个世界。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,几十年后,我会用笔墨把这片土地的变迁写进书里。
2018年我开始写《浦东史诗》时,特意回了趟当年被救的地方。外滩的万国建筑还在,对岸的浦东已经立起了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,上海中心大厦像根银针插入云端。站在江边,我突然觉得,曾祖父扛过的木头、父亲划过的船、我漂过的水,其实都在一条时间线上——浦东的开发不是凭空冒出来的,是无数普通人的汗水和梦想堆起来的。这种感觉,让我写每一个字时都觉得沉甸甸的。
上观新闻:家族记忆与个人经历,对您书写浦东有什么特殊意义?
何建明:太重要了。如果没有这些亲身经历和家族故事,我写的可能只是一本“浦东建设说明书”,而不是有温度的历史。写《浦东史诗》时,我去采访陆家嘴的老居民,听他们说“以前这里是烂泥渡路,下雨天能陷到膝盖”,我立刻就想起爷爷说的“曾祖父在泥里扛木头”的场景。这种跨越百年的呼应,让我明白“发展”从来不是抽象的词,是一辈辈人把“不可能”变成“可能”的过程。
有一次,我去探访“和记码头”旧址,现在那里是陆家嘴滨江公园的一部分。一位在公园扫地的阿姨告诉我,她爷爷以前就在这码头上扛活,“那时候扛一袋米能换两个烧饼,现在我扫公园,一天能挣两百块”。这种个体命运的变化,比任何GDP数据都更能说明浦东的进步。所以我总说,我的笔不仅要写“大事”,更要写“小事”——因为大事都是由小事堆起来的,就像浦东的摩天大楼,地基是无数普通人的脚印。
上观新闻:您既在浦东有长期生活的沉淀,又能以相对抽离的视角审视它的发展,这两种身份带来的不同观察维度,是如何在您的书写中相互交织、互为补充,让浦东的形象更立体的?
何建明:我觉得我来到这里,也是看到我的前辈还没有完成的任务。浦东的建设,我用文字参与其中。这种参与让我摸到了浦东的发展脉搏,也像是踏着前辈的足迹,看到这片土地从曾经的小渔村,变成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,而且按照中国的发展势头,它可能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一个舞台中心。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为故乡去书写、去抒发情感吗?这就是我的情怀。

浦东开发开放大景航拍,浦东陆家嘴航拍。
我把自己的经历、家族的故事融入书写,能更真切地捕捉到浦东的精神——那种从历史深处延续下来的闯劲、包容和不断向前的动力。而作为观察者,我又能跳出个人情感,系统地梳理浦东从初级发展到党的十八大以后发展的历程,看清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。这两种视角结合,让我既能钻进浦东的肌理,感受它的温度,又能站在高处,看清它的方向,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更真实、更有力量。
从史诗到新史
上观新闻:《浦东史诗》已经全景展现了浦东开发的起点与激情,《浦东新史》作为续篇,在内容上有哪些突破性的拓展?
何建明:如果说《浦东史诗》是“打地基”,写的是浦东从一片农田到现代城区的“破局”,那么《浦东新史》就是“盖高楼”,聚焦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浦东如何从“跟跑”到“领跑”的质变。这八年里,我几乎把浦东当成了“第二故乡”,光是采访笔记就记了三十多本。
如果说拓展,我觉得是“维度的延伸”。《浦东史诗》里,我更多写的是基础设施建设、金融贸易如何“从零起步”——比如陆家嘴第一根桩基怎么打、外高桥保税区第一家外资企业怎么来的。但《浦东新史》里,我更关注“软实力”的成长。比如张江科学城,我不仅写了芯片研发的技术突破,还跟踪了一群“张江男”的生活:他们在实验室睡折叠床,却会记得给保安师傅带热包子;有个博士为了攻克基因测序技术,三年没回老家,他母亲来上海看他,在实验室外站了两个小时,最后只远远看了一眼他忙碌的背影。这些细节,让“科技创新”不再是冷冰冰的术语,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。
前滩的变迁特别能体现这种“质变”。很多人知道前滩被称为“第二个陆家嘴”,但我更想写的是它如何平衡“繁华”与“生活”。在那里的滨江公园,老人在栈道上打太极,年轻人在咖啡馆里讨论创业方案,还有妈妈推着婴儿车看江景——这种“闹中取静”的状态,是浦东发展到新阶段的写照:不再只追求“速度”,而是思考“如何让城市更像家”。

市民在前滩滨江踏青露营,感受惬意自由的慢生活。
上观新闻:与传统的上海地方史相比,您的书写还有哪些独特视角?
何建明:传统的地方史大多是“事件脉络+数据”,这当然重要,但少了点“人气”。我想做的,是给历史“注入体温”——让读者能从字里行间闻到汗水的味道、听到机器的轰鸣、感受到人的喜怒哀乐。
比如写外高桥保税区,我不仅记录了七次“封关”的政策突破,还跟踪了一家日本物流公司的中国区总裁。他1992年带着3个员工来上海,在仓库里吃了半年泡面,最大的愿望是“能在办公室里装个空调”;到2023年,他看着女儿在浦东的国际学校毕业,用流利的上海话说“这里比东京更像故乡”。
我还特别关注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《浦东史诗》出版后,有位老工程师找到我,说当年建设南浦大桥时,工人们发明了“沉井施工法”,但没人记录。他从床底下翻出一本泛黄的日记,里面记着“1991年7月15日,江面温度42摄氏度,泡了3小时,算出了钢筋的受力数据”。在《浦东新史》里,我专门补写了这段:一群农民工出身的技术员,用算盘计算力学数据,在江上泡了三个月,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。这些“无名者的史诗”,才是浦东真正的底气。
上海的灵魂与风骨
上观新闻:在您笔下,上海的城市精神始终是暗线。这种精神究竟是什么?它如何塑造了浦东?
何建明:上海精神的核心,我觉得是“海纳百川的包容”与“精打细算的务实”的共生,再加上一股“敢为天下先”的闯劲。早年间,我的曾祖父能在码头立足,靠的就是这种精神——既敢接纳外来的新技术、新规矩,又能把每一分力气都用在实处。
我在《浦东新史》里写到一个细节:外高桥保税区第一次“封关”时,铁丝网围栏比海关要求低了30厘米。就这30厘米,开发区的人连夜返工,三天三夜没合眼,硬是把3.35公里的围栏全部加高达标。他们说“这不是差几厘米的事,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脸面”。对“标准”的较真,对“规矩”的敬畏,就是上海精神里“靠谱”的底色。
上观新闻:您在书中多次提到“爱城市才能发现美”,这种因爱而生的感知,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?
何建明:上海人对城市的爱,不是空洞的口号,是藏在细节里的。我认识一位老市政工人,退休后每天骑着自行车巡查滨江大道,看到地砖松动就记下来报给物业,看到垃圾就弯腰捡起。他说:“这地方建得这么好,弄脏了心疼。”这其实是上海精神里的“共建共享”。
反观有些作家,总盯着城市的阴暗角落,觉得“写龌龊才深刻”。但上海人不这样,他们相信“爱才是改变的动力”,对城市的共情力比任何批判都更有建设性。
上观新闻:也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浦东应对各种挑战吧。
何建明:支撑浦东应对各种挑战的精神,核心在于不断向前的“动词精神”——上海是个动词,浦东更是如此。我们出门叫“上街”,做饭叫“上灶”,“上”是一个动作,这体现了上海最早的文化特质。
同时,浦东的发展承载着“从芦苇荡到现代化大都市”的历史使命感,面对改革中的迷茫、外部的挑战,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进行自我挑战、与外界碰撞,凭借“无中生有”的魄力和对“东方世界舞台中心”的定位,在坚守中国智慧与价值观的基础上持续前行,相信“每一天都是新的”,在磨难中走向成熟。
上观新闻:“从芦苇荡到现代化大都市”,这一跨越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深意?
何建明:芦苇是浦东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意象。当年英国人来到浦东时,这里还是一片芦苇荡,象征着殖民时期中国的落后与荒芜;而今天,浦东在这片土地上“种植新的芦苇”,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与新世界建设。我采访前滩的规划师,他办公室里摆着个玻璃罐,装着工地的第一捧土,土上插着三根芦苇。他说,前滩可以盖100栋高楼,但不能少了这丛芦苇——它提醒我们,城市是从滩涂里长出来的。
这种对照既是历史的呼应——从殖民时代的被动到当代的主动,更是文学与哲学的对话:同样的土地,因发展道路的不同,生长出了完全不同的“芦苇”。
文学如何为城市立传
上观新闻:作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,您一直强调报告文学对城市书写的价值。在您看来,这种体裁为何适合记录浦东这样的地方?
何建明: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在于“真实”与“深度”的平衡。它不像新闻报道只停留在事件表面,也不像小说可以虚构,而是要“贴着地面飞行”——既要有扎实的史料支撑,又要有文学的感染力。浦东的故事太特殊了,它不是缓慢生长的自然演进,而是一场“压缩式”的革命,三四十年走完了别人百年的路。这种剧烈的变迁里,藏着太多需要被“打捞”的细节。
我的写作都要力求和情感的联结,不管我写什么地方,我都要想和我的共鸣在哪里?让我有感触的地方是什么?城市是有灵魂的,报告文学能做的,就是用具体的人、具体的故事,让这个灵魂显形。
上观新闻:“文学要为城市存档”,这种“存档”与地方志、纪录片有什么不同?
何建明:地方志是“骨架”,纪录片是“影像”,而报告文学是“带体温的档案”。它不仅记录“发生了什么”,更要追问“为什么发生”“人在其中经历了什么”。写世博园建设时,我找到一位拆房工人,他手里有本“砖日记”,每块砖上都标着原主人的姓氏:“张家的砖,李家的瓦,拼起来才是浦东的家。”这种对“根”的敬畏,是冰冷的档案不会记载的。
我写浦东,就是想让后人知道:这座城的光荣里有无数普通人的汗水,它的未来也等着无数普通人去创造。当读者觉得“这也是我的故事”,城市的精神才算真正传下去了,这比任何纪念碑都结实。
上观新闻:上海的海派文化里有“兼容并蓄”的特质,这与报告文学“既要真实又要生动”的要求,有没有内在的呼应?
上观新闻:海派文化就是“不挑食材,能做出好菜”,苏州人的精细、宁波人的敢闯、洋人的技术,都能在这儿融成新东西。报告文学也是这样,它既要像新闻一样“真”,又要像小说一样“活”,既要学国外纪实文学的笔法,又要扎中国的土——这种“兼容”的本事,跟上海骨子里的“海纳百川”是一路的。报告文学能从“特写”变成“立传大器”,靠的都是这种“不设限、敢融合”的劲儿。
上观新闻:在AI写作兴起的今天,您认为文学创作,尤其是报告文学,该如何自处?
何建明:AI能处理数据、模仿结构,但它永远学不会“共情”。我曾让AI写一段“浦东开发的艰辛”,它罗列了工期、数字,却写不出一位工程师在大桥合龙时,摸着钢筋说“这上面有我儿子的胎毛”——这种私人化的情感,是文学的不可替代性。
但我们也不能排斥技术。我用大数据分析了浦东三十年的政策关键词,发现“改革开放”的出现频率与GDP增长曲线高度吻合,这为我的叙事提供了新视角。数字化工具可以做“减法”,帮我们筛选信息;但“加法”必须靠人——把冰冷的数据转化为滚烫的故事。
上观新闻:您觉得未来的城市书写,应该有哪些新的探索?
何建明:要“接地气”,也要“有锐度”。现在的城市发展太快,作家不能只做“记录者”,更要做“瞭望者”、做“数字时代的田野调查者”。我写浦东的数字贸易时,不仅看了海关的电子通关数据,还跟着一位跨境电商主播跑了三天:看她凌晨五点选品,对着镜头用三种语言介绍国产家电,深夜打包时在包裹里塞手写的感谢卡。她说:“屏幕那头是活生生的人,不是数据流。”这句话点醒了我:数字化再快,终究是为人服务的,文学要做的,就是在代码与算法中,找到那些“人的痕迹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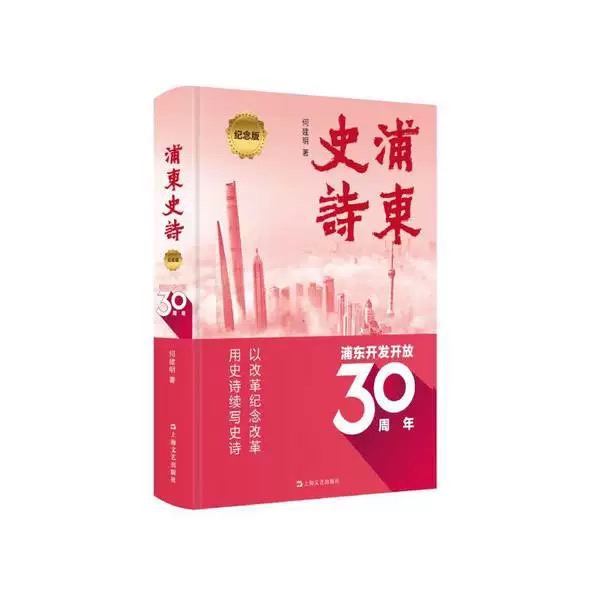
《浦东史诗》
何建明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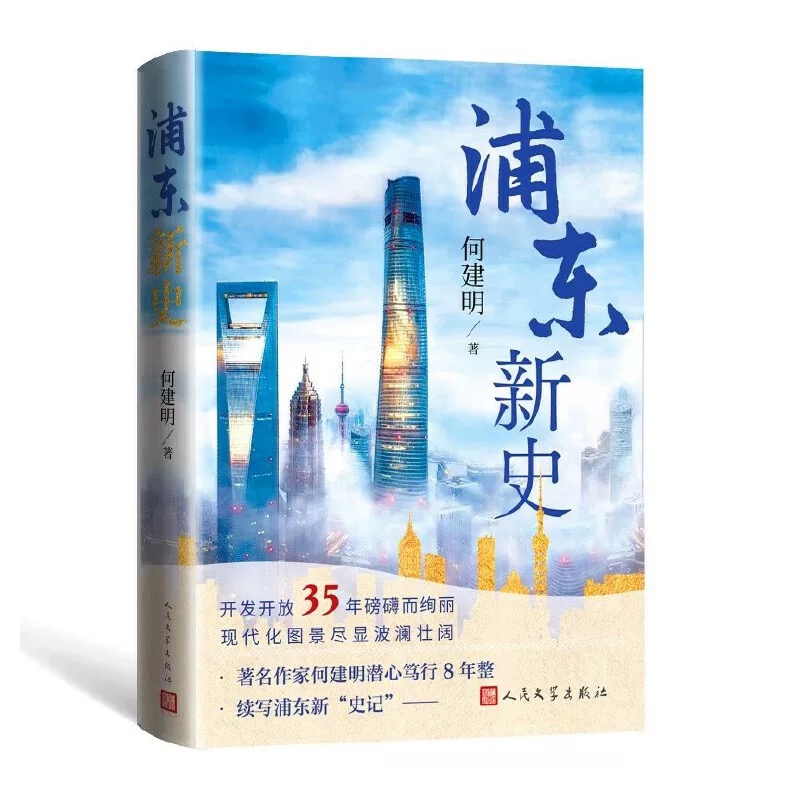
《浦东新史》
何建明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(文章来源:上观新闻)





